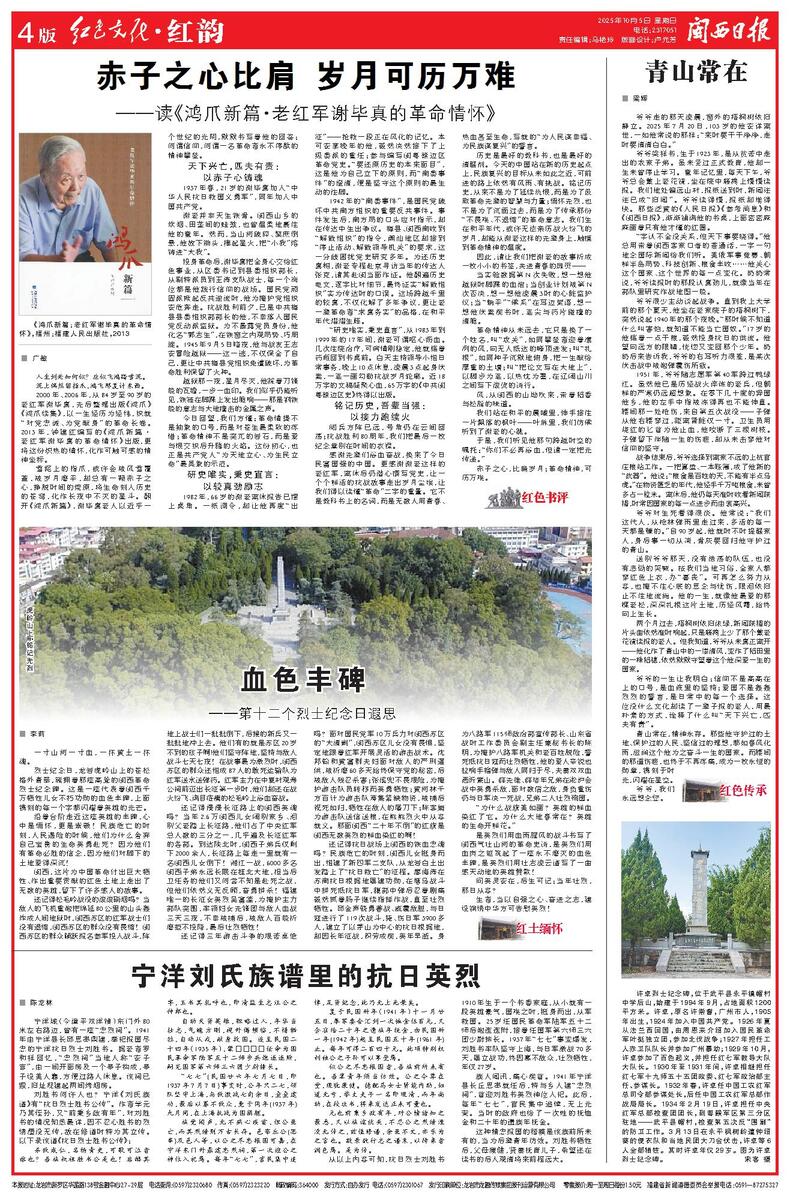青山常在
■梁辉
爷爷走的那天凌晨,窗外的梧桐树依旧静立。2025年7月20日,103岁的他安详离世,一如他常说的那样:“来时要干干净净,走时要清清白白。”
爷爷梁祥书,生于1923年,是从贫苦中走出的农家子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他却一生未曾停止学习。童年记忆里,每天下午,爷爷总会戴上老花镜,坐在院中藤椅上慢慢读报。我们地处偏远山村,报纸送到时,新闻往往已成“旧闻”。爷爷读得慢,报纸却堆得快。那些泛黄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闽西日报》,渐渐铺满他的书桌,上面密密麻麻画着只有他才懂的红圈。
“字认不全没关系,但天下事要晓得。”他总用带着闽西客家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国际新闻给我们听。美俄军事竞赛、朝鲜半岛局势、科技创新、粮食丰收......他关心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每一点变化。奶奶常说,爷爷读报时的那股认真劲儿,就像当年在部队里研究作战地图一般。
爷爷很少主动谈起战争。直到我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他坐在老家院子的梧桐树下,突然说起1940年的那个夜晚。“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知道不能当亡国奴。”17岁的他揣着一点干粮,毅然投身抗日的洪流。他望向远方的眼睛,恍惚又变回那个少年。奶奶后来告诉我,爷爷的右耳听力很差,是某次伏击战中被炮弹震伤所致。
1951年,爷爷随志愿军第40军跨过鸭绿江。虽然他已是历经战火淬炼的老兵,但朝鲜的严寒仍远超想象。在零下几十度的异国他乡,他的左手中指被冻得再也不能伸直。腰间那一处枪伤,来自第五次战役——子弹从他右腰穿过,距离肾脏仅一寸。卫生员用烧红的匕首为他止血,他咬断了三根树枝。子弹留下伴随一生的伤疤,却从未击穿他对信仰的坚守。
战争结束后,爷爷选择到离家不远的上杭官庄粮站工作。一把算盘、一本账簿,成了他新的“武器”。他说:“粮食是百姓的天,不能有半点马虎。”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经手千万吨粮食,未曾多占一粒米。离休后,他仍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时常因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由衷高兴。
爷爷对生死看得很淡。他常说:“我们这代人,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自90岁起,他就时不时提醒家人,身后事一切从简,骨灰要回归他守护过的青山。
送别爷爷那天,没有浩荡的队伍,也没有悲恸的哭喊。按我们当地习俗,全家人都穿红色上衣,办“喜丧”。可再怎么努力从容,也掩不住心底的思念与忧伤,眼泪依旧止不住地流淌。他的一生,就像他最爱的那棵老松,深深扎根这片土地,历经风霜,始终向上生长。
两个月过去,梧桐树依旧浓绿,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依然准时响起,只是藤椅上少了那个戴老花镜读报的老人。但我知道,爷爷从未真正离开——他化作了青山中的一缕清风,变作了稻田里的一株稻穗,依然默默守望着这个他深爱一生的国家。
爷爷的一生让我明白:信仰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是血液里的坚持;爱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是日常中的每一个选择。这位没什么文化却读了一辈子报的老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青山常在,精神永存。那些他守护过的土地、保护过的人民、坚信过的理想,都如春风化雨,滋润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而腰间的那道伤疤,也终于不再疼痛,成为一枚永恒的勋章,镌刻于时光,闪耀在星空。
爷爷,我们永远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