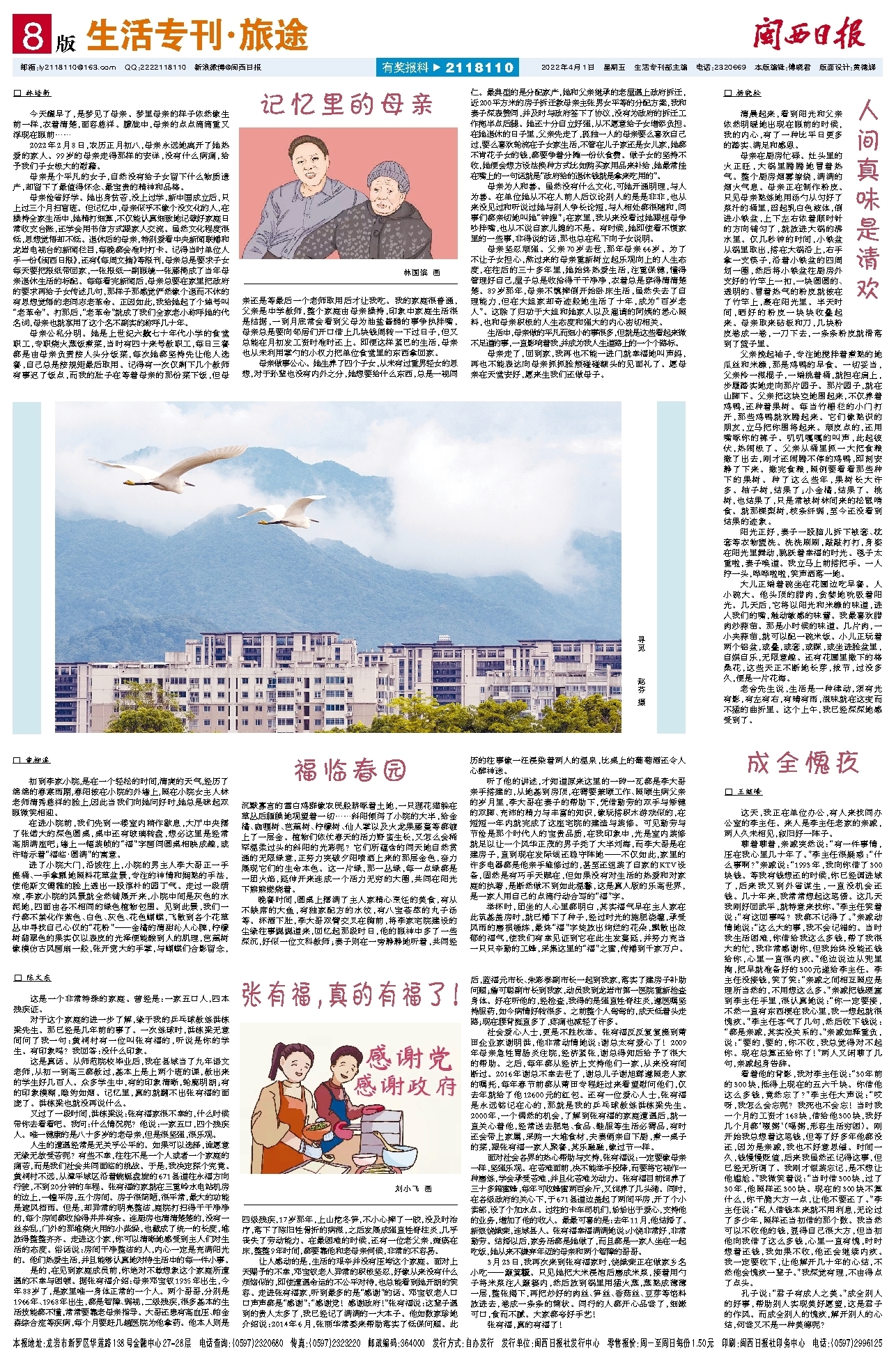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记忆里的母亲

林国滨 画
□ 林培新
今天醒早了,是梦见了母亲。梦里母亲的样子依然像生前一样,衣着清楚,面容慈祥。朦胧中,母亲的点点滴滴重又浮现在眼前……
202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家人。99岁的母亲走得那样的安详,没有什么病痛,给予我们子女极大的慰藉。
母亲是个平凡的女子,自然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留下了最值得怀念、最宝贵的精神和品格。
母亲俭省好学。她出身贫苦,没上过学,新中国成立后,只上过三个月扫盲班。但记忆中,母亲似乎不像个没文化的人,在操持全家生活中,她精打细算,不仅能认真细致地记载好家庭日常收支台账,还学会用书信方式跟家人交流。虽然文化程度很低,思想觉悟却不低。退休后的母亲,特别爱看中央新闻联播和龙岩电视台的新闻栏目,每晚都会准时打卡。记得当时单位人手一份《闽西日报》,还有《每周文摘》等报刊,母亲总是要求子女每天要把报纸带回家,一张报纸一副眼镜一张藤椅成了当年母亲退休生活的标配。每每看完新闻后,母亲总要在家里把政府的要求再给子女传述几句,那样子那感觉俨然像个退而不休的有思想觉悟的老同志老革命。正因如此,我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老革命”。打那后,“老革命”就成了我们全家老小称呼她的代名词,母亲也就享用了这个名不副实的称呼几十年。
母亲公私分明。她是上世纪六欸七十年代小学的食堂职工,专职烧火蒸饭煮菜,当时有四十来号教职工,每日三餐都是由母亲负责按人头分饭菜,每次她都坚持先让他人选餐,自己总是按规矩最后取用。记得有一次仅剩下几个教师有事迟了饭点,而我的肚子在等着母亲的那份菜下饭,但母亲还是等最后一个老师取用后才让我吃。我的家庭很普通,父亲是中学教师,整个家庭由母亲操持,印象中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一到月底常会看到父母为油盐酱醋的事争执拌嘴,母亲总是要向邻居们开口借上几块钱周转一下过日子,但又总能在月初发工资时准时还上。即便这样紧巴的生活,母亲也从未利用掌勺的小权力把单位食堂里的东西拿回家。
母亲做事公心。她生养了四个子女,从未有过重男轻女的思想,对于孙辈也没有内外之分,她想要给什么东西,总是一视同仁。最典型的是分配家产,她和父亲继承的老屋遇上政府拆迁,近200平方米的房子拆迁款母亲主张男女平等的分配方案,我和妻子深表赞同,并及时与政府签下了协议,没有为政府的拆迁工作拖半点后腿。她还十分自立好强,从不愿意给子女增添负担。在她退休的日子里,父亲先走了,孤独一人的母亲要么喜欢自己过,要么喜欢轮流在子女家生活,不管在儿子家还是女儿家,她都不肯花子女的钱,都要争着分摊一份伙食费。做子女的坚持不收,她便会想方设法换种方式比如购买家用品来补给,她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政府给的退休钱就是拿来吃用的”。
母亲为人和善。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她开通明理,与人为善。在单位她从不在人前人后议论别人的是是非非,也从来没见过和听说过她与别人争长论短,与人相处都很随和,同事们都亲切地叫她“钟嫂”;在家里,我从来没看过她跟祖母争吵拌嘴,也从不说自家儿媳的不是。有时候,她即使看不惯家里的一些事,非得说的话,那也总在私下向子女说明。
母亲坚忍顽强。父亲70岁去世,那年母亲66岁。为了不让子女担心,熬过来的母亲重新树立起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往后的三十多年里,她始终热爱生活,注重保健,懂得管理好自己,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衣着总是穿得清清楚楚。89岁那年,母亲不慎摔倒开始卧床生活,虽然失去了自理能力,但在大姐家却奇迹般地生活了十年,成为“百岁老人”。这除了归功于大姐和她家人以及雇请的阿姨的悉心照料,也和母亲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大的内心密切相关。
生活中,母亲做的平凡而细小的事很多,但就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一直影响着我,并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路标。
母亲走了,回到家,我再也不能一进门就幸福地叫声妈,再也不能表达向母亲抓抓脸颊碰碰额头的见面礼了。愿母亲在天堂安好,愿来生我们还做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