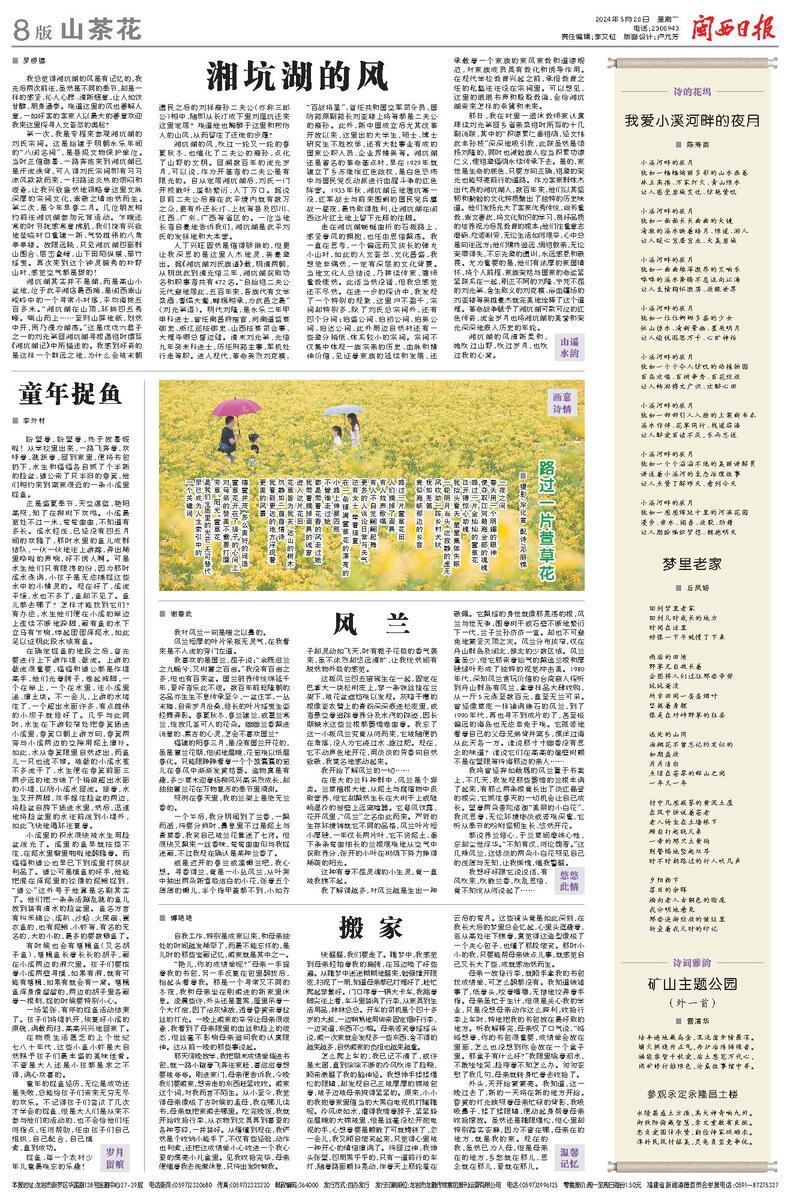搬家
■傅艳艳
自我工作,特别是成家以来,和母亲独处的时间越发稀罕了,而最不能忘怀的,是儿时的那些宝藏记忆,搬家就是其中之一。
“艳儿,你的成绩单呢?”母亲一手提着我的书包,另一手反复在包里翻找后,抬起头看着我。那是一个寻常又不同的冬夜,我和母亲坐在刚搬进的新家里休息。凌晨些许,外头还是墨黑,屋里吊着一个大灯泡,因了沾灰缘故,透着昏黄带着拉丝的灯光。一晚上搬家的辛劳让母亲很疲惫,我看到了母亲眼里的血丝和脸上的疲态,但丝毫不影响母亲追问我的认真眼神。这从前一晚的那些事说起。
那天傍晚放学,我把期末成绩单揣进书包,就一路小跑着飞奔往家赶,喜滋滋着想要被夸夸。刚进家门,母亲便告诉我,今晚我们要搬家,想带走的东西赶紧收收。搬家这个词,对我而言不陌生。从小至今,我觉得母亲像极了古时候的孟母,我在哪儿读书,母亲就把家搬去哪里。吃完晚饭,我就开始收拾行李,从衣物到文具再到喜爱的各种零碎,一并装好。从懵懂到现在,我俨然是个收纳小能手了,不仅有些经验,动作也利索,还把这成绩单小心收进一个我心爱的漂亮小礼盒里。见我收拾完毕,母亲便催着我去洗漱休息,只待出发时喊我。
快醒醒,我们要走了。睡梦中,我感觉到母亲轻拍着我的肩膀,在耳边唤了好些遍。从睡梦中迷迷糊糊地醒来,勉强撑开眼皮,扫视了一周,知道母亲都已打理好了,赶忙爬起穿戴好。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我踮着脚尖往上看,车斗里装满了行李,从家具到生活用品,林林总总。开车的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一边娴熟地用绑带固定捆好行李,一边笑道,东西不少嘛。母亲苦笑着摇摇头说,搬一次家就会发现多一些东西,舍不得的越来越多,自然搬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怎么爬上车的,我已记不清了,或许是太困,直到徐徐不断的冷风吹冻了脸颊,顺带激醒了我的脑神经。我想伸手揉揉惺忪的眼睛,却发现自己正被厚厚的棉被包着,被子边被母亲掖得紧紧的。原来,小小的我抱着家里值当的大黑白电视机打瞌睡呢。冷风凉如水,灌得我缩着脖子,紧紧躲在温暖的大棉被里,但是丝毫没松开抱电视的手,心想着要是颠散了可就糟糕了,忽一会儿,我又顾自傻笑起来,只觉得心里被一种开心的情绪填满了。待回过神,我伸头张望,四周黑乎乎的,只有一道前行的车灯,随着路面颠抖晃动,伴着天上那轮羞在云后的弯月。这些镜头竟是如此深刻,在我长大后的梦里总会忆起,心里头逗趣着,若从高处往下瞧着,真觉得这造型像极了一个夹心包子,也懂了那股傻笑。那时小小的我,只要能帮母亲做点儿事,就感觉自己又长大了些,成就感油然而生。
母亲一放稳行李,就顺手拿我的书包找成绩单,可怎么翻都没有。我知道做错事了,低着头,咬着嘴唇,无措地绞弄着手指。母亲虽忙于生计,但很是关心我的学业,只是没想母亲动作这么麻利,收拾行李上车时,特地把我的书包放在最好取的地方。听我解释完,母亲叹了口气说,“妈妈想着,你的书包很重要,成绩单会放在里面,怎么也没想到你会放在一个盒子里。那盒子有什么好?”我眼里噙着泪水,不敢哇哇哭,脸垮着不知怎么办。匆匆安慰了我几句,母亲就转身忙着去收拾了。
外头,天开始蒙蒙亮。我知道,这一晚过去了,新的一天将在新的地方开始。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母亲忙碌的背影,我吸吸鼻子,揉了揉眼睛,便动起身帮着母亲收拾摆放。虽然还是睡眼惺忪,但心里却特别踏实安静,因为不管在哪,母亲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现在的我,虽然已为人母,但是母亲在的地方,乡愁就在那儿,思念就在那儿,爱就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