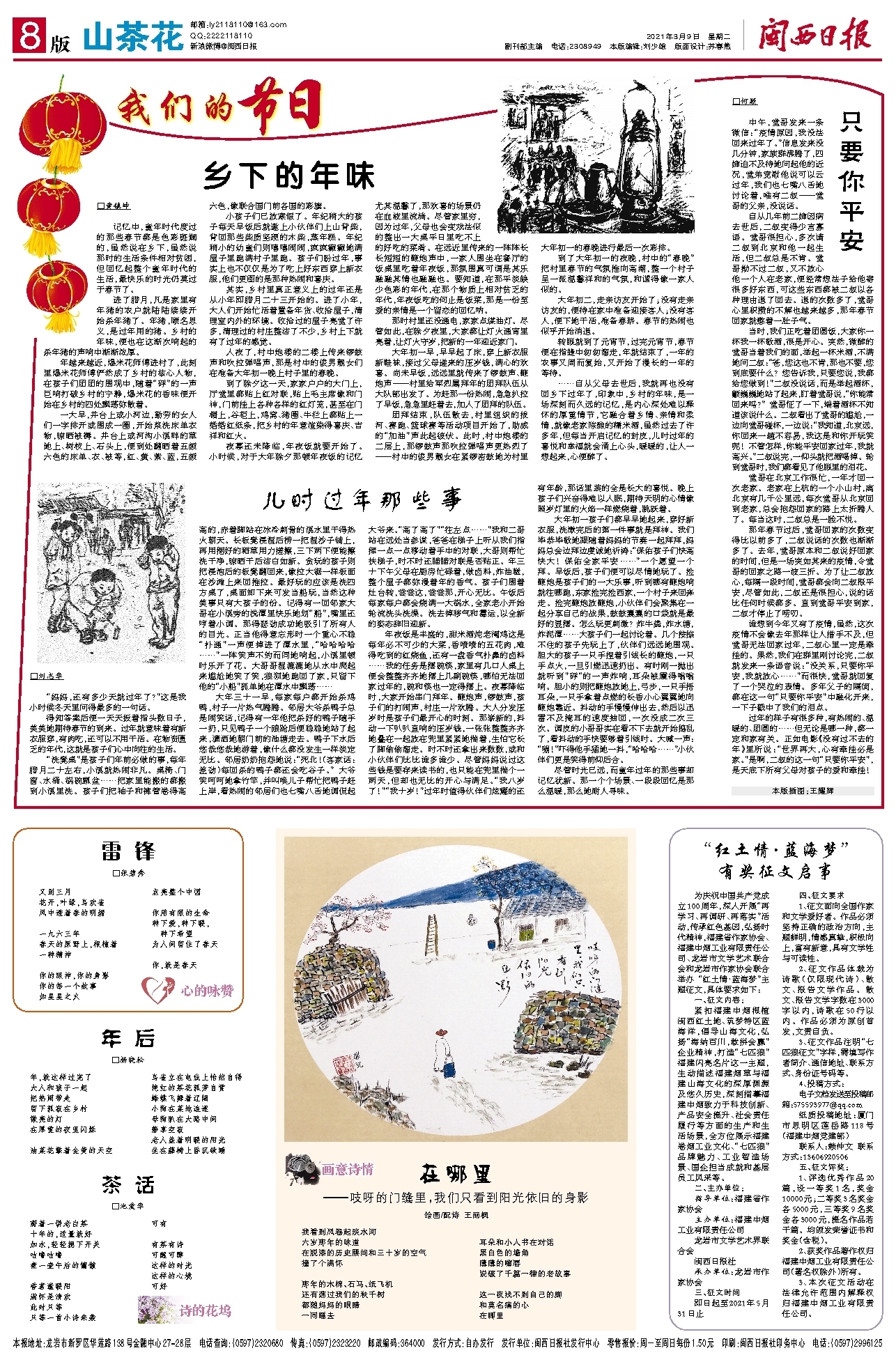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乡下的年味

□黄镇坤
记忆中,童年时代度过的那些春节都是色彩斑斓的,虽然说在乡下,虽然说那时的生活条件相对贫困,但回忆起整个童年时代的生活,最快乐的时光仍莫过于春节了。
进了腊月,凡是家里有年猪的农户就陆陆续续开始杀年猪了。年猪,顾名思义,是过年用的猪。乡村的年味,便也在这渐次响起的杀年猪的声响中渐渐浓厚。
年越来越近,爆米花师傅进村了,此刻里爆米花师傅俨然成了乡村的核心人物,在孩子们团团的围观中,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打破乡村的宁静,爆米花的香味便开始在乡村的四处飘荡弥散着。
一大早,井台上或小河边,勤劳的女人们一字排开或围成一圈,开始浆洗床单衣物,晾晒被褥。井台上或河沟小溪畔的草地上、树枝上、石头上,便到处翻晒着五颜六色的床单、衣、被等,红、黄、紫、蓝,五颜六色,像联合国门前各国的彩旗。
小孩子们已放寒假了。年纪稍大的孩子每天早饭后就邀上小伙伴们上山背柴,背回那些柴质坚硬的木柴,蒸年糕。年纪稍小的幼童们则嘻嘻闹闹,疯疯癫癫地满屋子里跑满村子里跑。孩子们盼过年,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为了吃上好东西穿上新衣服,他们更图的是那种热闹和喜庆。
其实,乡村里真正意义上的过年还是从小年即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进了小年,大人们开始忙活着置备年货、收拾屋子,清理室内外的环境。收拾过的屋子亮堂了许多,清理过的村庄整洁了不少,乡村上下就有了过年的感觉。
入夜了,村中炮楼的二楼上传来锣鼓声和吹拉弹唱声,那是村中的俊男靓女们在准备大年初一晚上村子里的春晚。
到了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厅堂里都贴上红对联,贴上毛主席像和门神,门前挂上各种各样的红灯笼,甚至在门楣上,谷柜上,鸡窝、猪圈、牛栏上都贴上一绺绺红纸条,把乡村的年意渲染得喜庆、吉祥和红火。
夜幕还未降临,年夜饭就要开始了。小时候,对于大年除夕那顿年夜饭的记忆尤其温馨了,那欢喜的场景仍在血液里流淌。尽管家里穷,因为过年,父母也会变戏法似的整出一大桌平日里吃不上的好吃的菜肴。在远近里传来的一阵阵长长短短的鞭炮声中,一家人围坐在餐厅的饭桌里吃着年夜饭,那氛围真可谓是其乐融融其情也融融也。要知道,在那平淡缺少色彩的年代,在那个物质上相对贫乏的年代,年夜饭吃的何止是饭菜,那是一份至爱的亲情是一个留恋的回忆呐。
那时村里还没通电,家家点煤油灯。尽管如此,在除夕夜里,大家都让灯火通宵里亮着,让灯火守岁,把新的一年迎近家门。
大年初一早,早早起了床,穿上新衣服新鞋袜,接过父母递来的压岁钱,满心的欢喜。尚未早饭,远远里就传来了锣鼓声、鞭炮声——村里给军烈属拜年的团拜队伍从大队部出发了。为赶那一份热闹,急急扒拉了早饭,急急里赶着去,加入了团拜的队伍。
团拜结束,队伍散去,村里组织的拔河、赛跑、篮球赛等活动项目开始了,助威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此时,村中炮楼的二层上,那锣鼓声那吹拉弹唱声更热烈了——村中的俊男靓女在紧锣密鼓地为村里大年初一的春晚进行最后一次彩排。
到了大年初一的夜晚,村中的“春晚”把村里春节的气氛推向高潮,整一个村子呈一派温馨祥和的气氛,和谐得像一家人似的。
大年初二,走亲访友开始了;没有走亲访友的,便待在家中准备迎接客人;没有客人,便下地干活,准备春耕。春节的热闹也似乎开始消退。
转眼就到了元宵节,过完元宵节,春节便在指缝中匆匆溜走,年就结束了,一年的农事又周而复始,又开始了漫长的一年的等待。
……自从父母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回乡下过年了,印象中,乡村的年味,是一场深刻而久远的记忆,是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厚重情节,它融合着乡情、亲情和柔情,就像老家陈酿的糯米酒,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每当开启记忆的封皮,儿时过年的喜悦和幸福就会涌上心头,暖暖的,让人一想起来,心便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