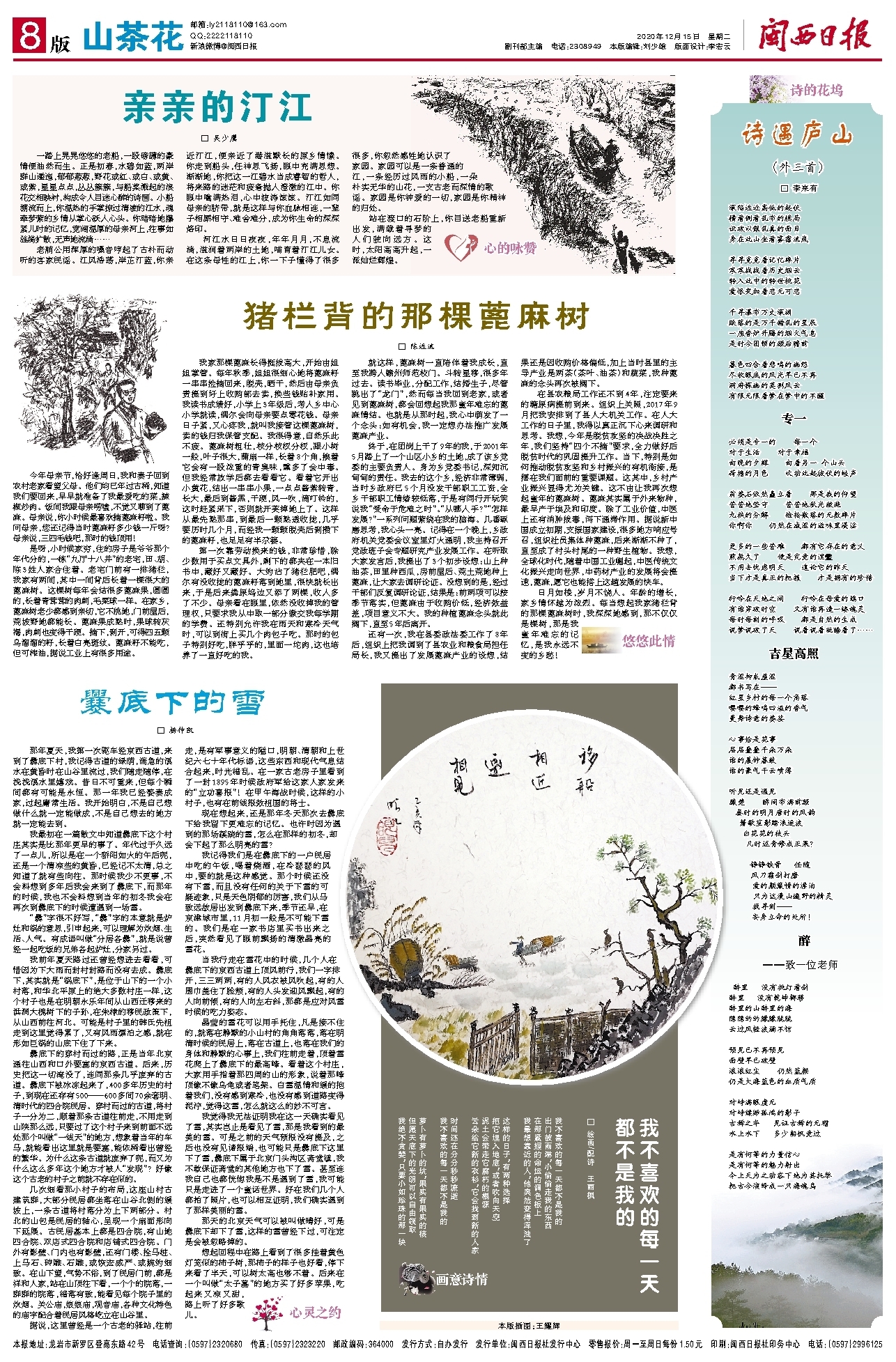猪栏背的那棵蓖麻树

□ 陈远流
今年母亲节,恰好逢周日,我和妻子回到农村老家看望父母。他们均已年过古稀,知道我们要回来,早早就准备了我最爱吃的菜,辣椒炒肉。饭间我跟母亲唠嗑,不觉又聊到了蓖麻。母亲说,你小时候最喜欢摘蓖麻籽啦。我问母亲,您还记得当时蓖麻籽多少钱一斤呀?母亲说,三四毛钱吧,那时的钱顶用!
是呀,小时候家穷,住的房子是爷爷那个年代分的,一栋“九厅十八井”的老宅,田、胡、陈3姓人家合住着。老宅门前有一排猪栏,我家有两间,其中一间背后长着一棵很大的蓖麻树。这棵树每年会结很多蓖麻果,圆圆的,长着青茸茸的肉刺,毛栗球一样。在家乡,蓖麻树老少都感到亲切,它不挑地,门前屋后,荒坡野地都能长。蓖麻果成熟时,果球转灰褐,肉刺也变得干硬。摘下,剥开,可得四五颗乌溜溜的籽,长着白亮斑纹。蓖麻籽不能吃,但可榨油,据说工业上有很多用途。
我家那棵蓖麻长得挺拔高大,开始由姐姐掌管。每年秋季,姐姐很细心地将蓖麻籽一串串捡摘回来,脱壳,晒干,然后由母亲负责提到圩上收购部去卖,换些钱贴补家用。我读书成绩好,小学上3年级后,考入乡中心小学就读,偶尔会向母亲要点零花钱。母亲日子紧,又心疼我,就叫我接管这棵蓖麻树,卖的钱归我保管支配。我很得意,自然乐此不疲。蓖麻树粗壮,枝分枝杈分杈,跟小树一般,叶子很大,蒲扇一样,长着8个角,挨着它会有一股浓重的青臭味,熏多了会中毒。但我经常放学后都去看看它。看着它开出小黄花,结出一串串小果,一点点酱紫转青,长大,最后到酱黑,干硬,风一吹,滴叮铃的,这时赶紧采下,否则就开荚掉地上了。这样从最先熟那串,到最后一颗熟透收拢,几乎要历时几个月,而经我一颗颗脱壳后剥攒下的蓖麻籽,也足足有半尕篓。
第一次靠劳动换来的钱,非常珍惜,除少数用于买点文具外,剩下的都夹在一本旧书中,藏好又藏好。大约沾了猪栏肥吧,偶尔有没收拢的蓖麻籽落到地里,很快就长出来,于是后来粪尿坞边又添了两棵,收入多了不少。母亲看在眼里,依然没收掉我的管理权,只要求我从中取一部分缴交我每学期的学费。还特别允许我在雨天和寒冷天气时,可以到街上买几个肉包子吃。那时的包子特别好吃,胖乎乎的,里面一坨肉,这也培养了一直好吃的我。
就这样,蓖麻树一直陪伴着我成长,直至我跨入赣州师范校门。斗转星移,很多年过去。读书毕业,分配工作,结婚生子,尽管跳出了“龙门”,然而每当我回到老家,或者见到蓖麻树,都会回想起我那童年难忘的蓖麻情结。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推广发展蓖麻产业。
终于,在团岗上干了9年的我,于2001年5月踏上了一个山区小乡的土地,成了该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身为乡党委书记,深知沉甸甸的责任。我去的这个乡,经济非常薄弱,当时乡政府已5个月没发干部职工工资,全乡干部职工情绪较低落,于是有同行开玩笑说我“受命于危难之时”。“从哪入手?”“怎样发展?”一系列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几番琢磨思考,我心头一亮。记得在一个晚上,乡政府机关党委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我主持召开党政班子会专题研究产业发展工作。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我提出了3个初步设想:山上种油茶,田里种西瓜,房前屋后、荒土荒地种上蓖麻,让大家去调研论证。没想到的是,经过干部们反复调研论证,结果是:前两项可以按季节落实,但蓖麻由于收购价低,经济效益差,项目意义不大。我的种植蓖麻念头就此搁下,直至5年后离开。
还有一次,我在县委政法委工作了8年后,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县农业和粮食局担任局长,我又提出了发展蓖麻产业的设想,结果还是因收购价格偏低,加上当时县里的主导产业是两茶(茶叶、油茶)和蔬菜,我种蓖麻的念头再次被搁下。
在县农粮局工作还不到4年,注定要来的糖尿病提前到来。组织上关照,2017年9月把我安排到了县人大机关工作。在人大工作的日子里,我得以真正沉下心来调研和思考。我想,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我们坚持“四个不摘”要求,全力做好后脱贫时代的巩固提升工作。当下,特别是如何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其中,乡村产业振兴显得尤为关键。这不由让我再次想起童年的蓖麻树。蓖麻其实属于外来物种,最早产于埃及和印度。除了工业价值,中医上还有消肿拔毒,泻下通滞作用。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支援国家建设,很多地方响应号召,组织社员集体种蓖麻,后来渐渐不种了,直至成了村头村尾的一种野生植物。我想,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工业崛起,中医传统文化振兴走向世界,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将会提速,蓖麻,愿它也能搭上这趟发展的快车。
日月如梭,岁月不饶人。年龄的增长,家乡情怀越为浓烈。每当想起我家猪栏背的那棵蓖麻树时,我深深地感到,那不仅仅是棵树,那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是我永远不变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