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文学永远是美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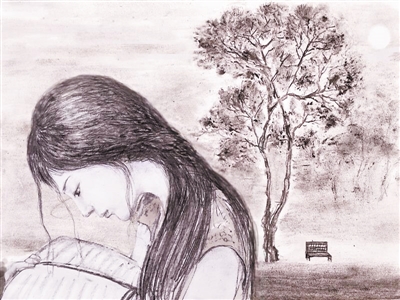
□吴子林
音乐家科伦布的爱妻亡故,他从此带着两个女儿隐居深林,整日在一个小木屋里独自研习古大提琴。在绵延无止的乐声中,他看见深爱的亡妻,此刻就坐在他对面聆听;之后,一起祷告,一起乘坐马车,一起并肩走过春色茂密的森林,一起来到河岸渡口,直到她独自坐上小船离去。怕她再次消失,他不忍停下手中乐曲。为了让她一遍一遍重现,他用余生不断拉奏心爱的大提琴,记下心里的悲伤乐曲,想看看爱将延续到哪里?
这是一个清静的世界。老房子旧得幽静、坦然,乐句绵延无休、难以捉摸,家中的器皿也都散发出乐器的光泽。科伦布在森林小屋里拉琴、作曲,在他眼里,王宫没有自己的木屋大,他拒绝宫廷表演的邀请,拒绝各种矫饰,只为灵感而作曲,只是记下瞬间的颤抖,删除多余的抒情。他的演奏闻名遐迩,在传说中更是出神入化。
有一天,17岁的红衣少年,一个鞋匠的儿子,敲响了音乐家的门。他自我介绍曾在国王的唱诗班唱了9年,还是中提琴演奏者,他立志成为伟大音乐家,而慕名前来学艺。红衣少年即兴演奏了《西班牙的罪恶》,科伦布听了十分生气:“为了取悦国王的音乐,不是用感觉演奏的音乐,只是让人快乐的装饰,不是真正的音乐!”红衣少年又演奏了自己作的一支曲,科伦布的心略有所动:“痛苦的声音才让我感动,而不是你的技巧。除了悲伤和眼泪,你在音乐中寻找什么呢?一个月后回来吧,那时我再决定收不收你!”
后来,红衣少年成了音乐家的学生;再后来,红衣少年背着老师受聘为皇家乐队的演奏家,而被逐出师门:“你在宫廷和市场演奏,就像去马戏团买一只马取悦自己!”这时,音乐家的大女儿爱上了红衣少年,偷偷将父亲传授的一切都教给了他。后来,为了一个“有利的位置”,红衣少年遗弃了她;再后来,红衣少年成了宫廷乐长,生活富足;音乐给他带来了华丽的马车,镶嵌珠宝的假发衣饰,显贵的地位与指挥权杖,但不再有17岁时眉宇间那湛蓝、清澈的眼光。然而,宫廷乐长深觉自己始终未得音乐的要领。他清楚地记得,年少的那个午后,在森林里听到科伦布的琴曲,那种庄重、静穆、悠远而哀伤的,才是真正的音乐。
老人弥留之际,宫廷乐长深夜赶赴到森林小屋,去上最后一堂音乐课。当他一身显阔地走进那简朴肃穆的木屋,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臃肿的丑角。他问老人:“音乐是什么?为了供奉上帝?为了取悦国王?为了金钱?为了荣誉?是爱情的忧伤?或是自暴自弃的放纵?”
都不是。
宫廷乐长终于领悟,自己的疑问便是答案:“是不是给死者的礼物?是给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低声的安慰?给那些消逝了的童年?是为了让鞋匠的锤声变得柔和,是为了那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过的时间,在我们呼吸之前,或者看见光亮之前……”
最后,老人与学生合奏自己久未示人的作品,彼此碰撞,彼此融合,彼此感应,彼此绽放,用爱感知音符——仿佛一起站在世界的高处,领略美的巅峰光彩,并肩凝望一次宛若新生的日出……
——这是法国电影《尘世里的每一个清晨》(Tous Les Martins du Monde)所讲述的三百多年前的故事,它让我们重温一种艺术人格全面熏染的师徒关系,影片里爱情与音乐相互阐释,其中的一切缓慢与静默,把我们带回到了音乐的黄金时代。
是的。倘若音乐真有魂魄的话,那就是它的毫无用处,它的“无用之用”。用音乐家科伦布的话说,“音乐的存在是为了说出语言所无法说出的事物”。
倘若我们像红衣少年一样,总为现实中的财富、地位、成败、名誉等所左右,怎能不陷入孤单、惶恐和空虚之中呢?世界又怎么可能会生动起来呢?为诸色(物色、财色、器色、女色)为功名而艺术是可笑的,但从这些世俗的羁绊中挣脱出来,为自身的自由解放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音乐是爱,是诗,是虔诚,是恩慈,是馈赠,是内心孤独的吟唱,是出神的一瞬,是颤抖的瞬间,是人类关于光明、自由和宁静的力量的梦想。音乐是一种专注、耐心的修为,能将人变成一个内心强大而平和的人,生活由于此般修炼而清明透亮获得了尊严。
用罗曼·罗兰的话说,“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
文学亦然。
我离开故乡已二十多年。
世界因为有故乡才具有意义,都是没有家乡的人,这世界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具体家乡的故乡是不存在的,而故乡又是心、是灵魂,是有生动细节的。生老婚丧、百工劳作、节庆戏耍、衣食起居、鸟兽花草、人物肖像、道德文章,这些都是真实而广泛的存在,而礼仪、农具、服饰、艺术、民俗、建筑、雕像、书籍等,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或道具意义上的对象化存在,而是往往投射了诸多的人类情感和过往记忆;它们是时间箭镞的回响,是瞬息万变时间之物中较为恒定的标识物;它们不仅可以瞬时复活全部的历史记忆,还可以穿越未来之境。
一切都有自己的节律,总是自然生长、成形。作为魔性般的“志业”,写作首先是指向自我的行动,它关注灵魂的事实,针对自我的改变与疗救: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智生活。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是差不多的,都会经历一塌糊涂乃至死气沉沉的某个时期。在这“淬炼”中,我们审视与反思内心空洞的绝望,竭力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开启有关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而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掌控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这么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与此相应,那些从笔端缓缓流出的文字,记录下的便是我们心灵的足迹:从容不迫,不断向上,追求丰饶与美好。
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所言,“文学的目标在于: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言语活动中的旅程”;“每部作品都是一次旅行,一个行程,但它唯有借助内心的道路或路线,才能穿越外部的这条或那条道路”。在德勒兹看来,文学是一项健康的事业,“健康在于创造一个缺席的民族,创造一个民族”;“文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谵妄中引出对健康的创建或对民族的创造,也就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批评与临床》)。
时光起伏、交汇、交错,因之波澜荡起,因之梦想掀开,因之骨骼血肉顿生。对于一个内心有自己的领地、不想匍匐前行的人而言,盛装的青春、无谓的盛名甚至至高的权力,都算不了什么。即便世俗的风将人撞得踉踉跄跄,文学仍让人感觉风骨卓然。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写道: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
……
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我的故乡龙岩位于福建西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誉为“红色摇篮”。这里,崇文重教,文脉渊深,英才辈出。卓然独立、开疆辟域的风气极盛并赓续至今。只要你的根在这里,只要你的土壤在这里,没有谁能阻止你自由地绽放。只要你愿意,把生活的镰刀磨得锃亮,你可以成为梦里的任何一个人。时光旋转,岁月隆起或塌陷,你就像一棵小芽,兀自从山岩苍苔中迸出,渐渐长成参天大树,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我们真得感谢这片“红土地”!
在《新中国70年龙岩作家优秀作品选》“评论”卷里,我十分欣喜地读到了许多有生命、有灵魂的健康文字。诸多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从这里起步走向外面的世界,他们与作家、艺术家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倾听者、质疑者和审判员,都是在为这个“缺席的民族”而写作,而不单是历史的书写者、抄写者和打字员。他们把自己抛入时间和语言的洪流中,在健康中不懈创造,在创造中保持健康,最终寻到了自己的皈依之所。《新中国70年龙岩作家优秀作品选》的编选聚拢了龙岩70年来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不少佳作,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过去与传统。阅读“评论”卷里那些“锦心绣口”一般的文字,我们更好地理解、安放和扩展了自身,使未来的创造不至于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感谢故乡有识之士辛勤的劳作!
(吴子林,连城人。著名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系《新中国70年龙岩作家优秀文学作品选·评论卷》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